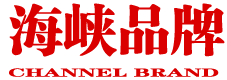戈壁深处的兵营
郑国光
1980年5月1日,我从师机关下派到驻防在戈壁深处的连队挂职,任副指导员。沿着河西走廊,一路西行,列车终于抵达玉门市低窝铺。踏上这片苍凉的土地,脑海里就想起王之涣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诗句。玉门关,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的关隘。其实,这里并非诗中所指的玉门关。玉门关史上曾三次东迁,最早是两汉通往西域的关隘,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城。王之涣的凉州词,则指陏唐时代二次东迁至瓜州境内的关隘,现遗址淹没在瓜州县的双塔水库之下。五代时期第三次东迁,至嘉峪关的附近,算是现在的所在地。
到团政治处报到后已近上午九点许。团里一时没有车送我到三连。我想时间尚早,便毅然决定徒步下连。政治处的干事告诉我,沿着眼前沙土路前行10余公里,3个多小时就能到连队,于是便背起被包就上路了。
沙尘暴
西域春晚,5月树上的枝芽刚刚苏醒,路边的骆驼刺才露出新芽,正逢春日暖阳,微风拂面,远方的祁连山下漂浮波状的气浪。心中充满渴望和期待,轻装上路,不多时,便置身于戈壁旷野中。

忽然间,发觉天边出现异样,在天地交界处蜿蜒着灰白色的气浪,由小到大、由慢到快、由远到近不断膨胀。眨眼间,就膨胀成一道翻涌的沙墙,像是万马奔腾扬起沙尘,带着断裂般呼啸,席卷而起。瞬间,我被卷进混沌的漩涡之中,沙暴不仅阻挡了前行的步伐,而且像是一个无形的手,反推你后退。我感觉到被推到一个畦地里,狂风卷着沙尘,层层覆盖过来,仿佛要将我吞没。顿时心中产生一丝恐惧,本能促使我不断探出头来,顾不得肌肤被沙石吹打的疼痛,顾不得沙尘蒙眼、呛喉、塞鼻的痛苦,在黑暗中不断挣扎着,第一次感到人生的无助。
正当感到自己将要被尘暴彻底吞噬的时候,风突然停了,尘沙缓缓的坠落,浑浊的天空慢慢放晴。还未落山的夕阳慢慢清晰起来,忽然有种换了人间的感觉。我的情绪从沮丧、失落中重新振着起来。我缓缓从沙尘中站起来,拂去沙尘肆虐后的狼藉,继续前行。

我曾一直在想这场尘暴之劫,是上天给我挂职锻炼的第一课。也许它要让你领悟人生的无常,学会应变之策。在生活中,我们可能摆脱不了命运的捉弄,但是,我们不妨坦然面对,欣然接受。在大自然面前,我们是渺小的个体,但是我们可以把握生存的智慧和信念,学会敬畏自然,尊重生命,不在自然伟力前屈服,可以满眼风霜,却是满心豪情,在无常命运中,坚守信念,勇敢前行。
兔子闹军营
三连所在地和周边戈壁环境相比算是富庶之地,它是冰山上的雪溶流经之地,雪水从地下隐蔽流敞,滋润着这片土地,这里水草肥美,遍地是名贵的甘草,还有“沙漠人参”之称的肉苁蓉。连队是以钢架土胚建成四合院构型的军营,矗立在空旷的戈壁上。军营旁低畦处还有一眼清泉,那是战士和戈壁黄羊等珍稀牲灵和平共享的水源。
到了连队,因为年轻,得到格外的呵护和照顾,我也很快溶入这个集体,成为建制中的一员。连队除完成日常训练科目外,生活略显枯燥和单调。我发现有一事项却能拨动战士快乐的心弦。

据说两年前,几个战士不知哪里弄来几只兔子,为了给这些小家伙安个家,战士们挖出一个两米见方,深约1.5米的坑。此后,照顾兔子成为战士闲暇时乐衷之事,大家轮流去周边割些鲜嫩的青草和嫩叶,精心喂养。
戈壁的草料带来的神奇的魔力,兔子迅速生长繁殖。由于此地戈壁地壤中水含量大,增强了沙土的粘合性力,很适应兔子在坑中横向打洞做窝。这样不出半年,一窝窝母兔带着小兔从洞里出来寻食。很是可爱。但是,不敢想象兔子繁殖速度惊人,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。不久,坑中四周已经布满了兔洞。显然容纳不下,只能在旁边如法复制兔坑。这样一来,兔子数量再度急增,不到一年功夫,数量已达数百只,成了连队改善伙食重要来源。我来下连的第一个晚上,连长、指导员为我压惊,款待我就是红烧兔肉。我第一次发现,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美的兔肉,原来兔子喂的草料常有甘草、肉苁蓉等名贵药材枝叶,汲取了沙漠精华,才有了这般得天独厚的美味。
相传连队有一个笑话,说是有一天,连队因故当天中餐蔬菜断档。为了救急,司务长急中生智,组织炊事班到野外采集刚露头的肉苁蓉。这时的肉苁蓉如春笋般的鲜嫩。炊事班将其切片,当作蔬菜打发中餐。可是,下午正逢队列训练,连长下达“立正”口令,结果战士弯腰曲腿,无法站立。可想而知年轻力壮的小伙,哪能经得起这般滋补。司务长的冒失,差点出了人命。后来听说,这里被国家列为珍稀药材保护地,而当时的我们真是暴殄天物。
好景不长,兔子超强的繁殖能力,带来了生态失控,兔子的地道已经遍布军营内外,不用投食,已经自主生存。糟糕的是,连队过冬的菜窑被打通了。事态的严重,不容置疑,周边的生态受到了严重威胁,无奈之下,全连不得不开展“打兔行动”,战士开动脑筋,发明各种捕兔工具和陷阱。后来我听说,通过一年多的行动,兔子基本消失。沉痛的教训,使连队官兵认识到保护脆弱生态的重要性。不再引进外来物种,成为连队铁律。
家书抵万金
戈壁深处,日子像是被风沙打磨过一般,单调且漫长。后来我发现,战士们还有一个反常的举动。在闲暇时,常翘首巴望通往连队沙石路。盼望那里出现“一骑红尘”,那是每天从团部过来的水车卷起的沙尘。水车不仅提供生活用水,也捎了家乡的书信。家乡人在信封收件人写着××市××信箱××号,可这个神秘的代号,又神奇送到这里,这种与世隔绝般的感受,只能依托书信承载着渴望和思念。

不难想象,在那金戈铁马的年代,那些西征的战士,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是如何解决乡愁和思亲的。也许在那冷月边关只能“碛见征人三十万,一时回首月中看”,靠望目寄托的无奈。还有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,那种阴阳两隔凄惨。当然现在的条件状况不同,但是靠一纸传递模式和思乡的情感是相同的。
书信的到来,成为官兵平凡日子里的慰藉。收到信的战士,脸上瞬间绽放久违的笑容,而没有收到信的战士,流露出失落的眼神,只能怀揣期待默默坚守。信是家的缩影,是战士脸上的“晴雨表”,也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抓手,有的战士因家中变故,情绪波动,指导员便以此为切入点,开展淡心活动,帮助他们入下包袱,重新投入紧张的训练和戍边的任务。
有一个炊事班姓张的东北兵,未婚妻嫌弃他当伙夫,没有技术,想与他断决婚姻关系,战士一时情绪低落。我了解情况后,主动介入。鼓励他回信,敞开心扉,亮明观点,描述炊事工作重要和他在战士眼里的价值,我也在他回信中夹上纸条。记得我是这样写的:炊事工作正是军地两用技术。小张现有的三级厨艺已得全连官兵的好评,依我的眼光看,凭他的聪明才智,加上努力,将来报考二级、一级、乃至特级厨师证的水平都挡不住。俗话说“识英雄于草莽”,你可得看准了,别后悔!我用这种生硬的语气,欲擒故纵,居然使姑娘回心转意。至此,小张倍加努力,勤奋研究食谱。特别是针对我连兔肉特色食材,做出了拿手的兔肉佳肴。名气一出,常被营团借用。情侣间情感与日俱增。
书信还是战士学习文化,提高语言表达、逻辑思维能力最实用的工具和平台,也成为每周班务会的主要议题。大家畅开思想,相互交流,甚至互看家信,群策群力,真正成为兄弟般情谊的纽带。1983年,我在空军上海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,曾以此为素材,写了题为《家乡日报》一文,用真挚的情感流淌在字里行间,老师给了优评,也感动了一班人。现在回到舒适的“温柔乡”里,已经表达不出当时的情感,总觉得意犹未尽,也许那种对家的思念,对书信的期待,早已超越文字本身,成为了军旅生涯中最温暖的记忆。